文化研究的参考书籍
 亲友益疏
亲友益疏文化研究和文化理论的区别是什么?
 其主君也
其主君也 娓娓而谈
娓娓而谈
文化研究和文化理论最大的区别当然是实践理论,你可以从书中得到,但是研究的话你要记要了解理论,又要对实际操作有一定的认识和动手能力,这可能是有一定难度的。我觉得区别就是当你做理论的时候,足够多的知识就可以,但是文化研究包含的就比较多了,可能需要做很多事情。
民族地区文化研究与图书馆在什么期刊容易发表
 灵蛇爱
灵蛇爱国外的茶文化研究著作,书刊,杂志
 克勤
克勤中国研究文化产业最权威的著作、文献、报刊杂志、论文是什么?或者最权威的作者是谁?
 复往邀之
复往邀之关于民俗研究和民俗文化的研究有哪些参考文献?最好多一点。
 天保
天保 殇
殇
《民俗文化与宗教信仰》,由色音主编,收入了在中国昆明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上发表的关于民俗文化、宗教信仰的论文,包括《元代蒙古族萨满教探析》《当代语境下的满族萨满教美术》《试析节日祭祀中的宗教文化内涵——以春节祭祀为例》《南岳信仰民俗初探》等。 民俗文化网 http://www.mswhw.cn/msfl/yj/index.html 《民俗文化研究》,共收录论文12篇,从理论视野、器具民俗和民俗生活三方面对中外民俗文化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其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民俗研究》,杂志创刊于1985年,是中国目前唯一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俗学理论刊物。 《民俗研究》杂志向国内外读者全面介绍中国民俗和民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国家确认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被认为是“能够代表中国民俗学最高学术水平的杂志。 季刊,每期272页,每季末月出版,全国邮局发行。来自:求助得到的回答
应该研究文化的哪些方面,如何研
 豫让
豫让 鼓腹而游
鼓腹而游
前回已经把文化的概念和内容说过。文化史是叙述文化的,懂得文化是什么,自然也懂得文化史是什么,似乎不用再词费。但我觉得前人对于历史的观念有许多错误,对于文化史的范围尤其不正确,所以还要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番。第一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法产生出来。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了走这条路,所以我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这一点,最近所讲演《历史统计学》等篇,也是这一路精神。但我们须知道,这种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简单说,整理史料要用归纳法,自然毫无疑义。若说用归纳法就能知道“历史其物”,这却太不成问题了。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这又为什么呢?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然则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我们常说历史是整个的,又作何解呢?你根问到这一点吗?依我看,什有九要从直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里头的最大关键,我现在还没有研究成熟,等将来再发表意见罢。第二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这条和前条,只是一个问题,应该一贯的解决。原来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从前只有自然科学得称为科学,所以治科学离不开因果律,几成为天经地义。谈学问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为“该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细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我前回说过:“宇宙事物,可中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看《什么是文化》)两系现象,各有所依,正如鳞潜羽藏,不能相易,亦不必相羡。历史为文化现象复写品,何必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门面?非惟不必,抑且不可,因为如此便是自乱法相,必至进退失据。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所以那书里头有一段说道:“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原著一七六叶。)我现在回看这篇旧著,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当时又因为调和这种见解,所以另外举出历史因果律与自然科学因果律不同的三点(原著一七七至一七九叶)。其实照那三点说来,是否还可以名之为因果律,已成疑问了。我现在要把前说修正,发表目前所见如下: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科学上还有所谓“盖然的法则”,不过“必然性”稍弱耳,本质仍相同。)“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再检查一检查事实,更易证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我们人类里头产出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名曰佛陀。为什么那个时候会产生佛陀?试拿这问题考试一切史家,限他说出那“必然”的原因,恐怕无论什么人都要交白卷!这还罢了,佛陀本是一位太子,物质上快乐尽够享用,原可以不出家,为什么他要出家?出家成道后,本来可以立刻“般涅槃”,享他的精神快乐,为什么他不肯如彼,偏要说四十九年的法?须知,倘使佛陀不出家,或者成道后不肯说法,那么,世界上便没有佛教,我们文化史上便缺短了这一件大遗产。试问:有什么必然的因果法则支配佛陀,令其必出家、必说法?一点儿也没有,只是赤裸裸的凭佛陀本人的意志自由创造!须知,不但佛陀和佛教如此,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文化现象,没有一件不是如此。欲应用自然科学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可是白费心了。“果”的方面,也是如此。该撒之北征雅里亚(今法兰西一带地),本来为对付内部绷标一派的阴谋,结果倒成了罗马统一欧洲之大业的发轫。明成祖派郑和入海。,他正目的不过想访拿建文,最多也不过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冲动,然而结果会生出闽粤人殖民南洋的事业。历史上无论大大小小都是如此,从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必然之果”。为什么呢?因为人类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他正从这方向创造,说不定一会又移到那方向创造去;而且一个创造又常常引起(或不引起)第二、第三……个创造。你想拿玻璃管里加减原素那种顽意来测量历史上必然之果,岂不是痴人说梦吗!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怎么解呢?谓互相为缘。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联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我们做史学的人,只要专从这方面看出历史的“动相”和“不共相”。倘若拿“静”的“共”的因果律来凿四方眼,那可糟了。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吗?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第三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我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毫无疑义,一直都认为是进化的。现在也并不曾肯抛弃这种主张,但觉得要把内容重新规定一回。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从物质文明方面说吗,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乃至如现代所有之几十层高的洋楼,几万里长的铁道,还有什么无线电、飞行机、潜水艇……等等。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虽然,细按下去,对吗?第一,要问这些物质文明,于我们有什么好处?依我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第二,要问这些物质文明,是否得着了过后再不会失掉?中国“千门万户”的未央宫,三个月烧不尽的咸阳城,推想起来,虽然不必象现代的纽约、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别体面处,如今那里去了呢?罗马帝国的繁华,虽然我们不能看见,看发掘出来的建筑遗址,只有令现代人吓死羞死,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远的且不必说,维也纳、圣彼得堡战前的势派,不过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那里去了呢?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所以拿这些作进化的证据,我用佛典上一句话批评他:“说为可怜愍者。”现在讲学社请来的杜里舒,前个月在杭州讲演,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大概说:“凡物的文明,都是堆积的非进化的;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又说:“够得上说进化的只有一条‘知识线’。”他的话把文化内容说得太狭了,我不能完全赞成。虽然,我很认他含有几分真理。我现在并不肯撤消我多年来历史的进化的主张,但我要参酌杜氏之说,重新修正进化的范围。我以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那么,历史进化说也尽够成立哩。以上三件事,本来同条共贯,可以通用一把钥匙来解决他。总结一句,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分配到这三个问题,得表如下:(自然系的活动)(文化系的活动)第一题 归纳法研究得出归纳法研究不出第二题 受因果律支配不受因果律支配第三题 非进化的性质进化的性质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杂志如何?该杂志如何投稿?
 乃凝于神
乃凝于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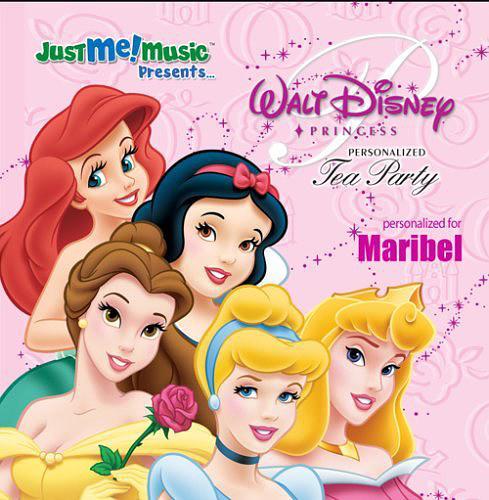 视舟之覆
视舟之覆
是经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发行的吗?有正规的双刊号吗?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于1980年创刊,杂志由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主管,赤峰学院主办的大型本科学报。2008年,经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批准同意,《赤峰学院学报》杂志由原来的额双月刊调整为月刊,页数为160页。杂志国际标准刊号为:ISSN 1673-2596,国内统一刊号:CN 15-1341/C,邮发代号为:16-158。是正规的学术期刊。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杂志征集什么类型稿件?红山文化研究、契丹辽文化研究、哲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文学研究 、 法学研究、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语言学研究、艺术研究。 该杂志有哪些期刊可以收录?中国知网全文收录吗?期刊收录情况: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2.请在首页地脚处注明作者姓名、学位、职称、研究方向,首页右上角注明联系电话。来稿为基金资助项目请注明何种基金资助项目或课题(并附编号)。3.编辑部对录用文稿将做技术性和文字性修改与加工。来稿发表后,赠送该期刊物。文稿自收到之日起2个月内未接到录用通知的,作者可另投他刊。不拟用稿件恕不退还,请自留底稿。5.论文末尾请详细注明作者工作单位地址、联系方式等,一遍我们能够及时快捷的与您取得联系。6.一般审稿期为1-3个工作日,逾期1个星期未接到用稿通知的,作者可回信咨询。7.文章通常在每天的下午3点之前集中送审。如着急刊发的作者,可尽早投稿。
帮我推荐几本文学评论的刊物
 德之至也
德之至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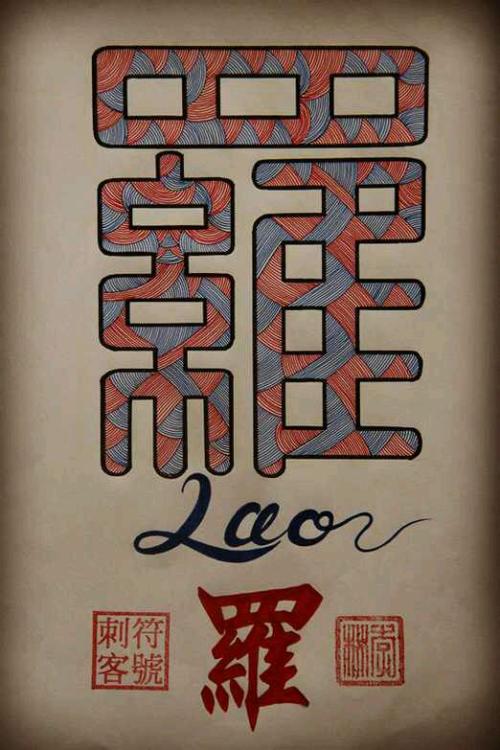 何基
何基
» 游客: 注册 | 登录 | 论坛向导 | 帮助 返回 学术论坛首页 Web www.xlmz.net 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 文艺评论 (Page:) » 狄更斯及其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狄更斯及其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作者: 标题: 狄更斯及其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梦的轻波 超级版主 积分 1080 发贴 866 精华 43 注册 2003-9-22 状态 离线 第 1 楼 字号 ---- 10pt 11pt 12pt 13pt 14pt 15pt 16pt 17pt 18pt 20pt 25pt 30pt 35pt 40pt 45pt 50pt 狄更斯及其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梦的轻波 2004-1-29 00:03 发表于: 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www.xlmz.net 作者:葛 桂 录 来源:http://sdxk.nttc.e.cn/sdxk/qkzx/00217.htm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南京大学,南京210093) -------------------------------- [摘 要] 20世纪上半叶狄更斯及其多部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后,大大促进了普通读者对这位英国小说家非凡生活经历、独特创作风格,以及不朽文学贡献的了解和把握。20世纪下半叶,我们对狄更斯的评价总是特别强调其作品内容的批判暴露性特征、对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同情,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局限性。不过,狄更斯小说的创作方法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去甚远。对其人道主义思想,我们也应该给予积极而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 狄更斯 人道主义 中国 接受 影响 [中图分类号]I 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JS07-005(2000)02-0114-07 [收稿日期] 2000-03-05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委社科基金项目《英国作家与中国》,课题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葛桂录,男,1967年生,淮阴师院中文系副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著有《比 较文学教程》(执行主编)等。 一、“善状社会之情态的迭更司” ——20世纪上半叶狄更斯在中国 在20世纪上半叶,每一个喜欢狄更斯作品的中国读者首先要感谢林纾,因为就是他最早把狄更斯领到了中国。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和翻译家,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学到中国的第一人,林纾之真正认识西方文学的妙处,也是在接触狄更斯之后,因而在其所有译作中,最重视的也正是狄更斯的小说。林纾从1907年到1909年间共翻译了狄更斯的五部小说:《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贼史》、《冰雪因缘》。[1]这几部译作被公认为林纾所有翻译作品中译得比较理想的小说。中国读者正是通过他的译品,才最早认识了英国这位久负盛名的伟大小说家。对我国新文学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林纾翻译介绍狄更斯小说五种并产生重要影响之后,民国时期又有一批翻译者陆续介绍了狄更斯的不少作品,深受人们喜爱。在长篇小说方面,薛一谔、陈家麟翻译了《亚媚女士别传》(上下卷,即《小杜丽》);魏易翻译了《二城故事》(即《双城记》);常觉、小蝶翻译了《旅行笑史》(上下卷,即《匹克威克先生外传》的节译本)[2]。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也有一些翻译介绍,有的作品还有多种译本。如狄更斯《圣诞故事集》中的一个中篇故事《圣诞欢歌》(A Christmas Carol )先后就有三个文言体译本、两个白话体译本和一个仿作改写本。其中,竞生的译本题作《悭人梦》刊于1914年《小说时报》21期;孙毓修的译本题作《耶稣诞日赋》刊于1915年《小说月报》5卷10号; 1919年上海东阜兄弟图书馆也出版了闻野鹤题为《鬼史》的译本;1928年上海商务馆出版了谢颂羔题为《三灵》的译本;1945年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方敬题作《圣诞欢歌》的译本。而根据狄更斯这个故事改写的一篇仿作则是天津人一鹃刊载于《礼拜六》杂志上的《一个侮辱圣诞节的人》(上、下)[3]。为大家竞相翻译或仿作的这个中篇小说,通过一个年迈而吝啬的商人从极端蔑视圣诞节日到虔诚信奉圣诞精神,从冷酷无情到最终变得温柔慷慨这样一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狄更斯相信人与人之间必须保存更多信任和爱的伟大思想,反映了大家的共同心声;加之这篇小说是通过三个幽灵去展开情节的,构思奇特,因而深受读者喜爱。 狄更斯的中篇小说《生活的斗争》(The Battle of Life)也是《圣诞故事集》中的一篇。这篇小说出现了周瘦鹃题为《至情》的文言体译本,以及陈原题为《人生的战斗》的白话体译本[4]。狄更斯的短篇小说《星》也有烟桥、佩玉的译本和周瘦鹃的译本[5]。周瘦鹃还翻译了狄更斯的其他小说,如《幻影》、《前尘》[6]等。 20年代以前也出现了一些有关狄更斯的介绍和评论文章。1911年《小说月报》第二年第四期上就刊登了一篇为纪念狄更斯百年诞辰而发行精美肖像情况的介绍文字。孙毓修在1913年《小说月报》4卷3号上著文则首先称狄更斯“非独著于一国,抑亦闻于世界。”并高度评价狄更斯小说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文中还特别介绍了狄更斯描写人物的特长,足见作者对狄更斯小说艺术魅力的赞赏溢于言表,同时也表明本世纪初期中国对狄更斯小说的认识、接受着重体现在其作品鲜明的社会功能和精湛的人物描写艺术这两个方面。 20年代也有不少对狄更斯作品的翻译介绍文字。1922年4月的《学衡》杂志第四期上刊有狄更斯的画像。1926年《小说世界》13卷14期到14卷25期连载了伍光建翻译的狄更斯名著《劳苦世界》(现通译为《艰难时世》),并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种,由上海商务馆于1926年12月出版了单行本,该书译者序概括了这部小说的特色及其重要价值。另外,1928年10月魏易自译自刊了狄更斯的另一部名著《双城故事》。沈步洲等译注的英汉合注本《二城故事》也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本时期对狄更斯的评价介绍也出现不少著述。谢六逸在《小说月报》13卷6号上的一篇文章就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狄更斯的创作情况。[7]文中把狄更斯称为继司各特之后描写社会贫困的最有势力的英伦第一小说家。《语丝》杂志刊载了德国批评家梅林格的《论迭更斯》一文。该文介绍了狄更斯这样一位最受德国人喜爱的大小说家,其具有旺盛创造力并确信民主主义、富于同情心的一面[8]。 周瘦鹃翻译了狄更斯的一些小说,同时他还多次向我们介绍了有关狄更斯的一些趣闻轶事。如《爱修饰的文学家》[9]就反映了狄更斯成名之后的一个生活侧面。同时,周瘦鹃在该文中还以狄更斯小说艺术创作特点为例说明做小说本非难事,“但须留意社会中一切物状。一切琐事。略为点染。少加穿插。更以生动之笔描写之。则一篇脱稿。未始不成名作。”并指出狄更斯这种小说取材的方法特点对自己创作产生的诸多影响等等[10]。 韩侍桁在《十九前半世纪英国的小说》一文中也认为狄更斯在英国文学中最与众不同。他有两种伟大的才干,即能够给死物加进人工的生气;能够象伟大的画家一般地捕捉与描绘人物的特形。文中特别强调狄更斯有一种讽刺家的才干,能够在刹那间观察出来某些奇异,而能生动地夸大地描画出来。[11] 与20年代相比,30年代出现了翻译介绍狄更斯的高潮。1930年上海北新书局印行的林惠元译《英国文学史》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狄更斯的生活经历、创作风格、重大功绩及其人道主义小说的显著影响等基本情况,书中称狄更斯作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和最独创的作家,用小说来唤醒人们提倡合于人道的对社会弊端的改革,因而他是文学中改革运动的领袖。1931年上海广学会翻译出版了美国清洁理女士所著的《迭更司著作中的男孩》一书。1933年吕天石《欧洲近代文艺思潮》(上海商务版)一书论及狄更斯时,也明确揭示出其作品中表现个人反抗社会的小说主题。1934年《国闻周报》上发表一篇题为《英国文坛新发现不列颠博物院秘档记——小说名家狄更斯夫人之泪史》的译述文章,则非常及时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狄更斯的情感经历、家庭生活中的不圆满状态以及在小说作品中的诸多表现,1935年《中学生》杂志55号上刊登的一篇朱自清写的《文人宅》(伦敦杂记之四),则带着我们参观了伦敦的狄更斯故居。1936年《文学》杂志6卷4号、6号上也载文介绍了英美国家纪念狄更斯成名作《匹克威克先生外传》发表百年的盛况。另外还有不少著作对狄更斯及其小说艺术作了详细介绍,如1935年出版的《西洋文学讲座》(英国文学部分,曾虚白著)、1936年出版的中译本《英国小说发展史》(Wilbur L.Cross原著)、1937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纲》(金东雷著)等。这些书籍也为我们全面了解和接受狄更斯作品提供了很大帮助。 1937年是狄更斯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这一年《译文》新三卷一期为此刊发了“迭更斯特辑”,翻译介绍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苏联批评家写的纪念文章《迭更司论——为人道而战的现实主义大师》。文章指出,狄更斯作为一个人道情感的提倡者,其小说描述了小人物的境遇,同时其作品也体现出了明显的思想矛盾性:“他要想除去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社会罪恶,但并不去触动这制度本身,因此产生了他那拥护明确的缓和办法的创作活动,因此产生了他那希冀劳资妥协和贫富妥协的倾向。这产生了他那些和解的‘圣诞故事’,这些和解的倾向反映着作为一个中等阶层的人道主义者的迭更斯的性格” [12]。作者认为此种和解的倾向正是狄更斯思想意识中的消极面。通过这篇译文,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苏联学术界对包括狄更斯在内的西方人道主义作家的总体评价标准,进而也为建国以后我国学术界评论这些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西方作家奠定了一个基调。《译文》新三卷一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克夫翻译的《年青的迭更司》一文,文章则向我们展示了狄更斯童年的苦难经历、青年的创业过程以及创作方面的独特才能。另外,该期《译文》还刊登了许天虹翻译的法国传记大师莫洛亚写的《迭更司与小说的艺术》。《译文》新三卷三、四两期又连续译介了莫洛亚的《迭更司的生平及其作品》(上、下)。后来1941年的《现代文艺》二卷六期上也继续译介了莫洛亚的《迭更司的哲学》。以上四部分正是莫洛亚传记名作《狄更斯评传》一书的全部内容。后来又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单行本(1943年7月版)。莫洛亚虽是法国人,但对狄更斯的理解似乎比大多数英国批评家还要深刻,而且有许多见解异常新颖,启人心智。因此,译介莫洛亚这部评传对我国读者全面深刻细致地认识狄更斯是功不可没的。 《译文》新三卷三期上还发表了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文章《我对迭更司所负的债》。另外,《译文》新三卷一期配合出版“迭更司特辑”,还刊发了有关狄更斯不同时期的肖像、生活、写作及住宅等方面的图片10幅。总之,《译文》杂志刊发的多篇译文及多幅图片为我们比较集中地了解狄更斯发挥了良好作用,也为30年代我国介绍狄更斯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40年代在狄更斯作品的翻译方面出现了新的高潮,而对狄更斯的评论和介绍文章虽不多见,但颇见新的角度。比如,朱维之就是从宗教的角度去接受和理解狄更斯及其作品的。他在《基督教与文学》一书中称狄更斯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家,笔下常流露着基督教的思想和感情,其许多作品的基础是建筑在《新约·福音书》之上的。[13]。林海则从比较的角度去分析评价狄更斯及其小说的创作特点。通过比较狄更斯与萨克雷的小说创作后,林海形象地指出:“迭更斯像一个宗教家,背着一面人道主义的大旗,站在十字街头说法,想以苦口婆心来挽回世道人心。萨克雷则俨然一个鲁克理细阿(Lucretius)派的哲学家,专门坐在十八层楼上的沙发里,俯着拖泥带水、蝇营狗苟的人群,顺便发出几声感慨,或来个会心的微笑”。但作者认为:“细想一下,坐十八层楼冷眼静观的萨克雷,要比站十字街头闭眼瞎说的迭更斯可靠一点” [14]。其他评论文章还有如蒋天佐是从翻译的角度论及了狄更斯小说语言运用方面灵活之极、丰富之极的特点[15];何家槐译的一篇文章则通过一个少年酷爱狄更斯小说的生动情形,充分展示了狄更斯作品不朽的艺术魅力[16];林海在另文中也介绍了包括狄更斯式人道主义在内的有关狄更斯及其作品的详细内容[17]。 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狄更斯作品颇为丰富。除以前各种译本不断得到再版外,还有不少是初版的译作。如邹绿芷翻译了《黄昏的故事》(收入六个短篇,1944年2月重庆自强出版社)和《炉边蟋蟀》(1947年11月上海通惠印书馆);《大卫·科波菲尔》有许天虹译本(1945年6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和董秋斯译本(1947年6月上海骆驼书店);《奥列佛·退斯特》有蒋天佐译本(1948年3月上海骆驼书店);《双城记》有海上室主译本(1940年4月上海合众书店)、许天虹译本(1946年1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和罗稷南译本(1947年5月上海骆驼书店);《匹克威克外传》有许天虹译本(1945年11月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和蒋天佐译本(1948年3月上海骆驼书店)等等。这些译本多数附有译者序或译后记之类的内容,比较详尽而深刻地介绍分析了小说家及其作品,这对指导读者理解认识和把握接受狄更斯大有助益。 总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翻译介绍狄更斯及其作品的基本情况如上所述。不过,狄更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无论在广泛性上还是在深刻性上,都比不上俄罗斯作家,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俄罗斯文学曾引起中国新文学先驱者们的巨大兴趣和热烈向往之情,其原因是由于中俄两国在国情上具有相似性,而促成中俄两国在文学上的亲密关系的深刻共鸣,这是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所无法比拟的。正是社会现实需要和文学本身的要求,使得中国作家群体对于俄国文学产生出这种喜爱和亲切感。相比较而言,包括狄更斯在内的其他欧洲作家在中国新文学作家心目中的地位要稍逊一些。而且狄更斯现实主义小说中那种理想主义的成分、浪漫主义的气息、人道主义的基调,也难以被主张为社会为人生的新文学家们普遍接受。更有在民族文化心理方面,中国作家接受狄更斯小说所展现的英吉利民族心理和文化生活时,也多少存在着某些心理隔膜。因此,狄更斯在本时期就无法达到全面而深刻自觉接受的程度。 二、“为人道而战的社会批判者” ——20世纪下半叶狄更斯在中国 建国以后涉及狄更斯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题为《狄更司笔下的美国》的译文,该文译自苏联刊物。文中谈及狄更斯1842年美国之行及其《游美札记》,认为狄更斯的美国见闻激起了他的愤怒和责难,《游美札记》则是控告美国社会组织与一切生活方式的起诉书,暴露了美国奴隶主的原形。同时文章也指出,狄更斯该书在今天仍未失去真实性,它所暴露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也属于这个世纪的美国,它目前正在幻想把整个人民变成服服贴贴的奴隶[18]。 我国对狄更斯的研究评价受到苏联学术观点的影响很大。苏联学术界在接受狄更斯时,特别强调其作品中的批判暴露性内容、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两面性,以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且鲜明地反对英美批评界对狄更斯的认识评价。这在1956年《文史译丛》创刊号上刊载的两篇译自苏联的文章《英国文学概要》和《关于狄更斯作品的评价问题》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后一篇文章的作者还说英国反动的批评家完全丧尽民族自尊心,完全不懂得爱护自己民族的伟大艺术,对其伟大遗产闭口不谈,或故意贬低歪曲,压抑其暴露性作品的意义,贬低他创造形象的批判意义,并对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问题避而不谈,而把他称为浪漫主义作家。进而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批评家无法揭示出狄更斯现实主义的真实内容及意义,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及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著作武装起来的苏联文艺学,才能给狄更斯创作以科学的评价[19]。受苏联学术界这种研究思路的影响,我国学者评价狄更斯的出发点及基本内容也大致如此。比如,全增嘏1954年写了《谈狄更斯》一文,其写作目的就是批驳英美批评家对狄更斯作品的弃绝态度。针对英美批评界认为狄更斯作品结构散漫、人物夸张、嘲笑露骨、感伤过分的看法,该文结合作品一一加以辩驳。文章最后也指出:“在今日之下来读狄更斯有重大意义。今天英美等国资本主义虽是在作垂死的挣扎,但仍然是很猖狂的。和资本主义做斗争,狄更斯仍然是我们的同盟军,仍然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力量。”[20] 紧接着以后的几年间,学术界和读书界都非常重视对狄更斯的介绍与研究,特别是在1957年和1962年发表了大量文章,形成了两次高潮。 1957年我国大量介绍狄更斯,是由几部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电影《匹克威克外传》、《孤星血泪》和《雾都孤儿》等在中国上演所引起的。为满足观众对狄更斯及其作品了解的浓厚兴趣,学者们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中国电影》和《大众电影》等多种报刊上纷纷撰文介绍狄更斯及其相关作品。尽管这些介绍都是一般知识性、鉴赏性的,但却为我国普通读者认识狄更斯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该年发表在《南大学报》第一期上华林一写的《谈谈狄更斯的“劳苦世界”》一文,分析了狄更斯的重要作品《艰难时世》。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所采用的社会政治历史批评方法,后来成为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评价西方作家的一种基本研究模式。 1962年是狄更斯诞辰150周年纪念,这更成为我国学者集中介绍评价狄更斯的一个契机,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了大批文章,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研究论文,由此也便形成建国后十七年中介绍和研究狄更斯的真正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学陈嘉、范存忠、姚永彩三位先生写的文章。陈嘉的论文《论狄更斯的〈双城记〉》也是针对英美资产阶级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在《双城记》理解与估价上的种种不正确、甚至故意歪曲的说法而写的。文中既驳斥了不少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企图贬低狄更斯而说他诋毁法国大革命的谬论,也指出由于狄更斯的阶级局限性和人道主义思想,使他对法国革命的历史过程采取一系列不正确、甚至根本错误的态度,但并未因此否定法国革命的正义性与必然性[21]。范存忠的论文《狄更斯与美国问题》则综述了狄更斯作品对19世纪中叶美国情况的反映以及对若干美国社会问题的认识情况,认为对美国社会尽情刻画和揭露,他提供的材料在不少方面比传统历史家所贡献的更真实更典型,有很大的进步意义。[22]姚永彩的论文《从〈艰难时世〉看狄更斯》在指出狄更斯揭露社会罪恶同情贫苦人民的痛苦不幸的同时,也表明他那种以情感与友爱作为改造社会现实的药方的做法,会引导人们脱离正确的斗争道路。文中也指出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有害的一面,即以抽象的爱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力图以阶级调和代替阶级斗争。[23]本时期全面分析狄更斯创作的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则是杨耀民发表在《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上的长达三万字的论文《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与思想特征》。 以上的一些评论文章都是侧重于思想内容分析的,而且又倾向于社会政治层面的探讨,由此得到的结论就显得大同小异。王佐良在1962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狄更斯的特点及其他》,则是当时唯一的一篇侧重于狄更斯小说艺术分析的文章。该文篇幅不长,却紧紧抓住狄更斯的创作特点,指出在其小说艺术里,真实的细节与诗样的气氛的混合,具体情节与深远的社会意义的混合,幽默、风趣与悲剧性的基本人生处境的混合,正是这一切使狄更斯的作品丰富厚实,而且充满了戏剧性。 总而言之,回顾一下建国以后十七年期间狄更斯在我国的接受情况,可以看出: 第一,对狄更斯的认识和评价受前苏联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在思想观点与研究方法论上都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去分析狄更斯作品的思想内容,特别强调的是其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暴露性,对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同情,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等等;同时也无不指出狄更斯的阶级局限性、宣扬阶级调和论、人道主义思想的两重性等内容,这由当时的政治气候与理论导向使然。 第二,对狄更斯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反驳英美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相关评价,认为以此可以捍卫狄更斯在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而介绍与评价狄更斯的另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古为今用,借此来认识看待现今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丑恶现实,着重看待的是狄更斯小说的认识价值和文献价值,对其审美价值多加忽视甚至排斥。其原因与当时中苏社会主义阵营与英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的国际政治形势有关,也使得对狄更斯的评价和接受就成为反英抗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起到了一种武器的作用,因此这一段时期的研究打上了鲜明的历史时代烙印。 “文革”以后,学术界对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杰出代表的狄更斯的介绍与研究出现新的高潮。1978年《外国文学研究》创刊号上王忠祥的文章《论狄更斯的〈双城记〉》,和1979年《读书》第二期上赵罗蕤的文章《批判的现实主义杰出作家狄更斯》都基本承续了文革前对狄更斯的总体评价,并为新时期以后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学术界评论狄更斯奠定了基调。 进入80年代,介绍和研究狄更斯的文章极多,并出现新的研究趋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涉及到的有关评论文章相当多,但毫无例外地都指出了它的两重性,而又凸现出其消极意义。有的文章评论中的“左”的倾向相当明显,这表明我们对狄更斯小说创作中的这种主导思想还应该尽量客观而深入地认识理解。 狄更斯在人物塑造上的卓越成就是人所共知的。这一时期就出现一些文章专门论及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问题。如任明耀探讨了狄更斯作品中别具一格的“怪人画像” [24];郭珊宝则认为狄更斯人道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即注意塑造儿童形象;[25]。其他还有文章谈及了狄更斯笔下的劳动人民形象、女性形象和扁平人物形象等问题。 关于狄更斯作品艺术特色方面的内容得到普遍重视,这方面的文章也很多。潘耀泉的文章首先比较早的对此作了总体论述[26]。李肇星、郭珊宝、王力在其文章中也都对狄更斯的小说作了细致阐述,富有启发意义[27]。 更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是,这时期评价狄更斯的作品,有些文章突破了传统定论,展示了更符合狄更斯小说创作实际情况的新认识。比如,《圣诞欢歌》作为一部充满人道主义思想的优秀作品,以往大多数评论都认为它提倡的是调和阶级矛盾的思想,而受到一致的批评否定。这种沿袭“阶级论”的过于简单的评论,到80年代初期受到挑战。郭珊宝在其文章中就认为这部作品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对人的性格的两重性的探索,是对人怎样丧失人性和怎样复归人性的探索。狄更斯的深刻之处在于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不仅在于阶级压迫与造成贫富对立,更在于摧残人性、摧残一切人的人性,而一切人性的沦丧,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弊端和更深重的创伤。一切人性的复归正是社会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狄更斯的同情不仅倾注在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且倾注于一切被迫丧失人性的人身上[28]。 与《圣诞欢歌》在以往得到的普遍否定性批评相比,狄更斯的另一部作品《游美札记》获得的则是一致的肯定性评论。人们只看到狄更斯在作品中对美国社会生活和制度各方面,特别是奴隶制的暴露批评的一面,而这与作品本身叙述的实际情况也有较大出入。张玲在为《游美札记》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狄更斯访美时值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显得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狄更斯笔下对当时美国社会某些进步方面所做的肯定,符合历史真实。而以往有些评论家只根据本人研究这部作品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需要,对书中所反映的狄更斯的对美国的看法加以不确切的诠释,诸如把狄更斯对美国某些监狱管理制度的批评夸大为反映“监狱制度的惨无人道”,把狄更斯对于当时美国国民性和社会风尚以及日常生活的一般介绍或略试品评解释为强烈的贬斥和指责,也有的又由于肯定和赞美当时美国社会的某些长处和优点,而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这是狄更斯思想局限性的表现,等等[29]。张玲的这些看法对我们重新客观评价狄更斯作品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朱虹在1982年到1984年的《名作欣赏》杂志上发表了有关狄更斯小说的一组赏析文章,涉及到狄更斯的绝大多数作品,这些文章后来汇集出版了单行本《狄更斯小说欣赏》(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名作欣赏》杂志还从1984年第4期起连载了朱延生翻译的莫洛亚所著《狄更斯评传》一书的内容,这些内容也汇以单行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11月出版。另外本时期出版的有关狄更斯的著述还有:罗经国所编《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张玲所著《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北京出版社1983年)、伊瓦肖娃的《狄更斯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赫·皮尔逊的《狄更斯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等。这些著作大大促进了狄更斯及其作品在中国的广泛普及和深入研究的进程,为狄更斯在中国的接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进入90年代后,也出版了不少有关狄更斯的传记,如埃德加·约翰逊的《狄更斯:他的悲剧与胜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和杰克逊的《查参考资料:http://www.xlmz.net/forum/viewthread.php?tid=3621

 40004-98986
40004-98986







